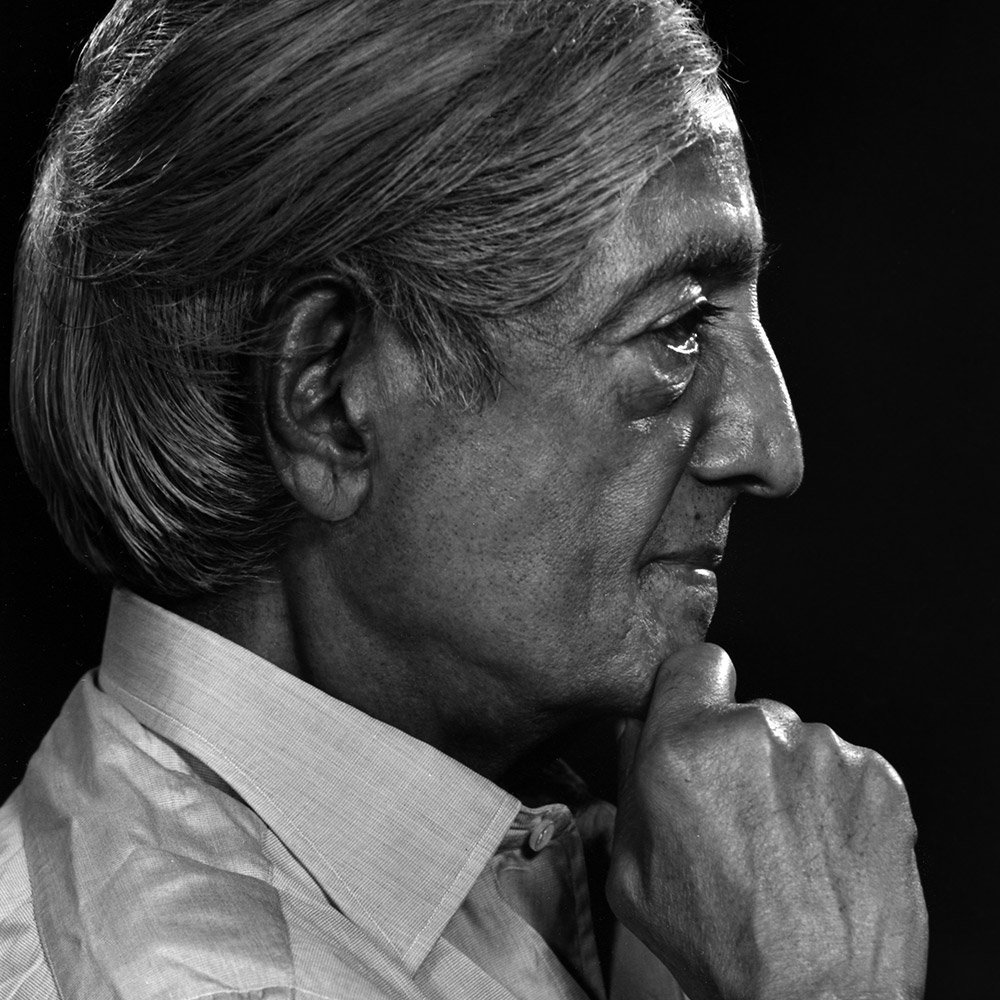
对于心理健康问题,过去人们一直讳莫如深,这种情况即使没有几个世纪,也有几十年了,而如今,人们却在大谈特谈心理健康。在疫情的特殊时期,我们很多人都遭遇了心理问题,隔离、焦虑、孤独、沮丧、沉迷、缺乏安全感、消沉、恐惧、担忧——这些都是克里希那穆提经常谈到的问题。克里希那穆提在演讲和讨论中向我们揭示,我们都对问题习以为常,并视之为个人的问题,这种态度或许存在着根本的错误。
而且,我们要认识到,比如,自己的孤独,其实是所有人所共有的,这点极其重要。只有这样,才能够理解并摆脱孤独,才能懂得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,拥有彻底的安全,保持身心安宁是怎么回事。
如何衡量心理健康,真正健康意味着什么?
“适应一个严重病态的社会并不是健康的衡量标准”,这句话可能是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最有名的一句克里希那穆提语录。尽管我们无法确知这是他的原话,但是,在几十年的时间里,克里希那穆提讲过类似的话,而且,这也是他反复重申的一个主题。那么,如果不谈社会,我们该如何衡量健康,特别是心理健康呢?真正健康意味着什么?正如我们将在这篇文章中看到的,克里希那穆提对于心理健康的见解远远超出了社会的看法,挑战着那些心理分析师、心理学家和宗教的狭隘的思考方式,揭示出一种无法撼动的秩序、和谐和清醒。
精神分析本是那些分析师的爱好,现在却受到了有钱人的追捧。你也许没去咨询精神分析师,但是,当你寄望某个宗教组织、某位领袖或者某项戒律,希望他们帮你摆脱迷恋、顾虑、心理情结的时候,你心里发生的过程是一样的,只是和心理分析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。这些方法也许在表面上会起些作用,但不可避免地都会发展出新的抗拒生活的心理障碍。任何人、任何技术都不会帮你摆脱这些限制。要想体验那种自由,你就必须深刻地理解生活,亲自了解这种制造和维持无知、幻觉的过程。这需要保持警觉,具有敏锐的洞察力,而不是仅仅接受一种技术。可是,人因为怠惰,就会依赖别人帮他理解生活,这样一来,他就会更感悲伤、困惑。理解这种无知的心理过程及其维持无知的那些活动,这种行动本身就可以带来深刻持久的幸福。
克里希那穆提1936年在纽约的第2次讲话

问:人是怎么变得神经质的?
克里希那穆提:我们怎样知道他们是神经质?注意,这个问题非常严肃。神经质——这是什么意思?是表现得有点儿怪异,头脑有点儿不清楚,感觉困惑,有点儿心理失衡,是吗?不幸的是,大部分人都有点儿心理失衡。不是这样?你不太肯定!如果你是基督徒、印度教徒、佛教徒或者是共产主义者,你的心理不就是不平衡的吗?如果你被自己的那些问题团团围住,给自己筑起一道围墙,因为你觉得自己比被别人强,你不就是神经质吗?如果你生活充满了抗拒,有着我和你,我们和他们等等各种分裂,那么你不就是心理不平衡吗?在办公室里,你想要表现得比别人更优秀,你不就是神经质吗?
那么,人是怎么变得神经质的呢?是社会让你神经质起来的吗?那是最简单的解释——我的父母、我们的邻居、政府、军队,所有人都让我神经质?他们都要为我的神经质负责吗?我向心理分析师寻求帮助,可怜的家伙,他也是神经质,跟我一样。拜托,请不要笑;这就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。那么,我为什么变得神经质了?正如现在这个世界里的一切,社会、家庭、父母、孩子,都没有爱。假如我们有爱,你认为还会有战争吗?你认为还会有这样的对你惨遭杀戮熟视无睹的政府吗?假如你的父母真的爱你,真的关心你、呵护你,教你如何待人和善,教你如何生活,如何爱,那么,就不会有这样的社会存在了。这些外在压力和要求导致了这个神经质的社会。我们内心还有内在的强烈冲动和固有的来自过去的暴力倾向,这些都助长了这种神经质、这种心理失衡。
选自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 YOU ARE THE WORLD (《世界在你心中》)
视频:我意识到我的行为很神经质,但神经质仍然存在。我该怎么办?
人能否摆脱痛苦?
什么是痛苦?人类为什么会痛苦?这是数百万年来最为重大的一个生活问题,只有非常非常少的几个人超越了痛苦。那些人成了英雄或拯救者,或者成了某种神经质的领袖、宗教领袖,然后他们便待在那个位置。而你我这些普通人,看来永远也无法超越痛苦。我们好像陷在痛苦里了。我们问,我们能否真正摆脱痛苦。
痛苦多种多样,有身体痛苦和各种痛苦的心理活动;有普通的疾病、年老、身体虚弱、饮食恶劣等造成的痛苦,也有广泛的心理痛苦。你意识到这个心理领域的存在了吗?你熟悉痛苦的结构、性质和作用吗?痛苦是如何运作的?其后果是什么?痛苦会让心灵残疾,让人越来越沉迷于自我中心的活动?你觉察到这些了吗?
我们在考虑这个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心理痛苦。一直以来,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渠道逃避痛苦——宗教、经济、社会活动、政治活动、商业活动等等各种逃避形式,还有吸毒——我们利用每一种逃避形式,却不去直面痛苦这个真实情况。心灵能彻底摆脱那些导致痛苦的心理活动吗?
造成这种痛苦的一个主要原因,就是一种孤立感,也就是感到完全孤独,感觉自己无可依靠,那是一种与任何人都没有联系,被完全孤立起来的感觉。你肯定有过这种感受。在某些瞬间,虽然你和家人待在一起,或者坐在公交车上,或者在参加聚会,你却有一种强烈的匮乏感、空虚感。这是一个原因。心理痛苦也是执着造成的,执着于一个观念或理想,执着于各种观点、信念,执着于一些人或概念。请在你自己身上观察这些东西。语言是给你看的镜子,向你展示你自己头脑的运作。所以要往那儿看。
看清孤独的全部含意
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巨大的失落感。失去威信,失去权力,失去如此之多的东西——失去你认为你爱的什么人。那是最大的痛苦。心能摆脱这一切吗?否则,无论它做什么,都不可能感受到一种对于整个生活的爱。生活不只是你的生活,而是全人类的生活,没有对于这整个生活的爱,就不会有同情心。没有同情心,你就永远也无法懂得爱是什么。
所以,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并超越痛苦。这是可能的吗?心灵能理解这种内心深处的孤独感吗?孤独和独处是有区别的。如果我们理解了孤独的意义,我们就会懂得独处意味着什么。当我们感到孤独时,那很令人害怕、沮丧,并且会引发各种情绪。你能否毫不躲闪地观察孤独,而不回避,不做合理解释?我感到孤独,随之而来出现了各种问题,比如逃避、依赖等等,这时,我能毫不躲闪地看着它吗?我能觉察孤独,不做合理解释,不试图找原因,而只是那样去观察吗?在那种观察过程中,我发现,逃避利用的是对于某种想法、概念或信念的依赖。我能否觉察到那种信念,并看到它是怎样成为一种逃避形式的?如果我安静地观察,这种逃避和信念就会消失,而我并没有费什么力气。
你一努力,就会出现观察者和被观察者,进而就会造成冲突。一旦你看清了孤独的全部含意,观察者就不存在了,而只存在你感到极其孤立这个事实。野心,贪婪,羡妒,渴望得到满足,想要成为什么人物,想要提升自己等等,我这些日常行为也会使自己感到孤立。我如此关注这个令人厌恶的渺小的自我,这种关注就是我的孤独的一部分。白天也好,睡觉也好,在所有活动中,我都这么关注我自己:我和你,我们和你们。我关注自己,忠于自己。我想为我自己做各种事,以我的国家的名义,以我的上帝、我的家庭的名义,以所有现在那些胡扯的名义。
所以,孤独产生于平日生活中的这种自我关注。在清楚了孤独的所有含意之后,我就看到了这些东西。我是看到的,而不是在创建理论。我看着什么的时候,那些细节就会呈现出来。我在仔细端详一棵树,或者在眺望河流、山峰,或者在看一个人时,在那种观察中,我就看到了一切。是它在给我讲;而不是我给它讲。所以,当你如此观察,如此毫无选择地觉察孤独时,孤独这个东西就完全消失了。
抛弃业已接受的传统,心灵就自由了起来
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依赖。我也许会依赖你们这些听众,因为你们在心理上喂养了我,令我兴奋异常,感觉自己特别重要,所以我有依赖。或者,我依赖某个人、某个想法、某种观点,依赖传统等等。心灵为什么会产生依赖?你可曾探讨过这个问题?它依赖家具、房子,依赖妻子、丈夫,天晓得还依赖些什么。为什么?这是给我们造成巨大痛苦的一个原因。我们依赖,可是我们发现依赖令人痛苦后,便想培养超然、冷漠,而那是另一件可怕的事。
那么,心灵为什么会依赖?依赖是心灵的一种消遣形式。假如我依赖你,我就会想着你;我会以我的自我中心的方式来关注你,因为我不想失去你。我不想让你自由;我不想让你做那种会妨碍我依赖的事。我在那种依赖中至少可以暂时感到安全。所以,在依赖中有恐惧、嫉妒、焦虑和痛苦。只是看看就好,不要说,“我该怎么办?”,你什么都做不了。假如你试图对自己的依赖做些什么,你就会制造另一种形式的依赖。所以,只是观察一下就可以了。你有依赖时,你会支配那个人,你想要控制他们,你会拒绝给他们自由。你若依赖,就完全否定了自由。
既然看到了孤独和依赖是导致悲伤的原因,那么,心灵能否摆脱孤独和依赖呢?这并不是要让心灵变得冷漠。我们关注的是整个生活,而不是仅仅关注我们自己的生活。因此,我必须回应生活整体,而不是只回应我那小小的欲望,想要靠你来帮我克服焦虑,消除痛苦。我们关注的是发现这种爱的品质,因为唯有心灵关注整体而非特定个体的时候,这种爱才会降临。当心灵关注整体的时候,就会有爱存在,然后,那个个体也会从整体中找到合适的位置。
那么,我的心、你的心、你的意识,有能力正视这个事实,看看它,看看它不仅给别人,而且给自己造成了多大的痛苦吗?只有结束痛苦,智慧才会降临。智慧不是你买书买来的,不是你从别人那里学来的。智慧来自对痛苦的理解,来自对痛苦所有含意的理解,痛苦不仅有个人的痛苦,而且还有人类的痛苦,这些都是我们造成的。只有超越了痛苦,智慧才会降临。
我们人类在心理上遭受了严重伤害。在学校,在家里,在工作中,我们内心深处都被自己或他人留下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伤害。我们受了伤,而那深深的创伤,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,都会令我们变得麻木迟钝。如果可以的话,请观察一下你自己的创伤。一个手势,一句话,一个眼神,就足以伤到你。你被拿来和别人比较时,你想要模仿某个人时,就会受伤。你如果遵循某种模式,就会受伤,不论那个模式是别人还是你自己设立的。所以,我们人类深受伤害,而那些伤害会导致神经质的行为。我们能否理解并摆脱这些伤害,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再受伤呢?我们能否抹除这些创伤,而不留下任何伤痕?请观察一下。不要看其它地方;看看你自己。你有这些创伤。你能抹除它们,不留任何痕迹吗?另一个问题,就是永不受伤。如果有创伤,你就不会敏感,你就永远不会懂得美是什么。你可以参观世界各地的博物馆,比较米开朗琪罗、毕加索,或者你喜欢的任何人的作品,研究这些人及其画作,做评论家,但是,只要人的心灵受到伤害,变得迟钝,就永远也不会懂得美是什么。没有美,就不会有爱存在。
痛苦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一种孤立感。
你的心受到了伤害,这时,它能否在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都不做反应?它能否了解到、意识到这些伤害?意识层面的伤害很容易就可以知道,不过,你能了解你那些无意识的伤害吗?还是说,你必须接受那些愚蠢透顶的分析。分析意味着有分析者和被分析者。谁是分析者呢?他不同于被分析者吗?假如不同,他为什么不同?是谁造成了这个不同于被分析者的分析者?假如他是不同的,那么他怎么会知道伤害是怎么回事呢?分析者就是被分析者。这不用说。要进行分析,每一次分析就必须是完全彻底的。如果有任何轻微的误解,你就无法进行彻底的分析。要分析,就必须要有时间:你可以分析一辈子,而且,你将在临死时还在分析。
那么,心灵该怎样才能发现那些内心深处的创伤,发现那些积累起来的种族创伤?征服者迫使被征服者屈服时,他就伤害了他。那就是种族创伤。帝国主义者、帝国的缔造者,给他所征服的那些人留下了深深的无意识的创伤。它就在那儿。心灵该怎样才能发现所有这些暗藏的创伤,发现那些深藏在意识角落里的创伤?我看到了分析的谬误,所以,分析并不存在。并没有分析这回事。我们的传统就是分析,但我抛弃了这个传统。那么,当心灵否定或抛弃了分析,看到分析的谬误时,它发生了什么情况?它就摆脱了那个负担。于是它就敏感了起来。它变得更加轻松,更加清楚,可以进行更为敏锐的观察。
所以,心灵抛弃业已接受的传统(分析、内省等等)之后,变得自由了。否定了传统,你就否定了那些无意识的内容。这种不曾意识到的东西就是传统——宗教传统,婚姻传统,啊,有许许多多传统。其中一个,就是认可伤害的传统,在认可伤害之后,再来分析伤害,消除伤害。而你在否定这个传统时,就否定了这些无意识的内容。于是你就摆脱了那些无意识的伤害。你不必做什么分析啦、梦的解析啦等等诸如此类的事。
这样,心灵抹除伤害,依靠的是观察伤害,而不是利用传统的工具——分析、讨论,你知道,所有现在那些事儿,群体疗法或个体疗法等等——凭借着对传统的觉察就抹除了伤害。否定了那个传统,你就不会受到那个传统的伤害。于是,心灵就会异乎寻常地敏感起来——心灵就是身、心、大脑和神经。这个整体敏感起来了。所以,现在心灵自由了。它超越了这种痛苦的感受。这是一颗摆脱了一切伤害的心灵,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再也不会受伤。奉承、侮辱,都动不了它。这不是说它给自己罩上了防护层。恰恰相反,它是完全不设防的。
克里希那穆提1974年在萨能的第5次讲话

问:你说分析否定了行动,这是什么意思?
克里希那穆提:什么是行动?看和做,不是吗?行动不是要分解开,先有想法,隔一段时间,再去行动。行动意味着做。做,不是做完或将做;而是正在做,在活跃的当下做。假如我有一个行动方案,那么在方案和行动之间就会存在一个间隔,就会存在矛盾,那样行动就总是不彻底的。同样,分析也在拒绝行动。
分析需要有时间。分析意味着分析者与被分析者之间的分裂。分析者进行分析,就是在推迟行动。分析者与被分析者存在分裂,分析就不会完整。而如果分析者就是被分析者,观察者就是被观察者,那么就会有完整的行动。
当我看到危险,比如看到悬崖、野兽、蛇等等的时候,我会立即行动,不是吗?因为心灵看到了危险。可是我们却看不到国家的危险,我们看不到宗教组织、信念、宣传的危险。所以,我们会继续这样生活。假如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危险,就会立刻行动。所以说,从分析这个词的深层意义上讲,它其实否定了行动——行动就是立即做任何事。
克里希那穆提1970年在佩鲁贾的演讲
视频:我该如何处理根深蒂固的情绪?
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
看看整个恐惧的模式,看看恐惧的后果及其相互影响的各种原因。你怕你的邻居,怕你的妻子,怕你的丈夫,你怕死,怕失业,怕生病,怕钱少,不够安度晚年,你怕你的妻子或丈夫私奔。就是恐惧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恐惧。恐惧,如果没有得到理解,就会导致各种形式的扭曲,导致精神疾病。那个人说,他像拿破仑一样伟大,他就是心理失衡了,这跟那个追随大师、追随古鲁的人,跟那个追求按照某些思想模式来生活的人是一样的。这些都是心理失衡,都是精神疾病。
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,在一个人们都患有精神疾病的世界里保持清醒是极其困难的。想一想,那些荒唐的教会和它们的教义、信仰——不只是基督教信仰,还有为无数人所珍视的印度教、伊斯兰教、佛教的信仰。这些都属于健康不良,都是源于恐惧的精神疾病。你也许会嘲笑天主教徒所信奉的教义,比如,圣母玛利亚肉身升天说。你说,“那多荒唐啊!”可是,你也有你自己的荒唐之处,所以,不要对此不以为然。我们知道恐惧的各种原因。我们了解那些异常微妙的恐惧。对一种恐惧进行仔细思考,比如对死亡的恐惧,对邻居的恐惧,对你的妻子或丈夫控制你的恐惧,这会不会为你开启那扇大门呢?这才是最重要的——而不是如何摆脱恐惧;因为一旦你打开了那扇大门,恐惧就给彻底消除了。
克里希那穆提1961年在孟买进行的讨论
问:解决心理问题的持久有效的办法是什么?
克里希那穆提:人的任何问题,都有三个认识阶段,不是吗?一是认识到问题的起因后果;二是认识到问题的矛盾对立过程;三是认识到自我并体验到思想与思想者是一体的。
拿你的任何问题来说:比如,愤怒。觉察一下愤怒的生理、心理原因。愤怒也许来自神经疲惫、神经紧张;也许是因为受到了某种思想感受、恐惧、依赖或者渴望安全等等引发的条件作用的影响;也许来自身体上或是感情上的痛苦。大部分人都知道这种对立面的冲突,可是,由于冲突带来了痛苦或烦扰,我们本能地就想要摆脱冲突,或者以简单粗暴的方式,或者以各种微妙的方式。我们关注的是逃避而不是理解这种斗争。这种想要摆脱冲突的渴望强化并延续了冲突,于是,会使得矛盾继续存在下去。我们必须观察并理解的,正是这种渴望。然而很难在二元冲突当中既听其自然又保持觉察;我们要么谴责,要么辩护,要么比较,要么认同;所以我们总在选边站队,这样一来,就是在维持造成冲突的原因。如果你想超越这个问题,那么就需要无选择地觉察对立面的冲突,这虽然非常艰难,却是必不可少的。
克里希那穆提1945年在奥海的第5次讲话
完全和谐的心灵
做梦是在延续你白天里的活动,延续白天的思想活动,延续白天的焦虑,延续白天感受到的孤独、焦虑和恐惧。你在睡梦中用各种符号进行着同样的活动。观察一下你白天里的生活,这种生活是混乱的,有心理上的依赖,有如此多的伤害,你会看到,这些东西会延伸到睡梦中。假如你在白天的生活井然有序,你还会做梦吗?秩序是观察失序,不是由社会、恐惧、宗教裁判或者根据你对秩序的设想而整顿出来的人为秩序,那种秩序会变得机械呆板。
大脑只有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运转。你可以在某种神经质的信念或行为中,或者在某种神经质的状态中找到安全。而真正的秩序出现在你的生活完全有序之时。你需要非常密切地观察自己生活中那些心理上、外在上的混乱,只有那时,这种完全的秩序才会出现。有了完全的秩序之后,你也许还会做些表面的、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梦,可是,你的心却是完全放松的,会在醒来时感到神清气爽。
在完全的秩序中睡眠,意味着身心是完全和谐的。有了完全的和谐,心灵就可以在睡眠中让自己重新焕发活力,变得朝气蓬勃、天真无邪。天真无邪,是指心灵永远也不会受伤。唯有这样一颗完全和谐的心灵,唯有这样的心灵才会理解那无法衡量的事物。
